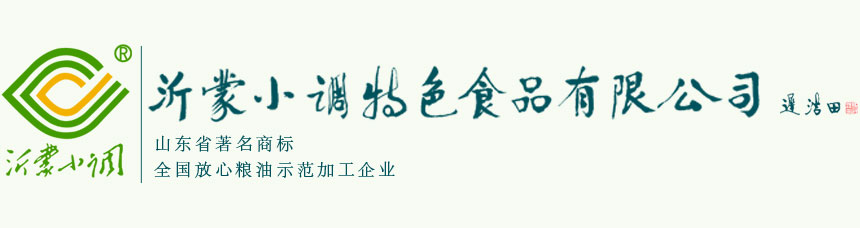有一份情怀,只能在记忆中回味,童年那些令人回味无穷的童年趣事,你还记得多少呢?
我的童年时光,是在费县探沂镇三南尹老家度过的,那时候父亲在方城粮管所工作,母亲和我们兄妹留在老家。住着三间毛草屋,没有楼上楼下,没有电灯电话,更没有听说过空调、电视,更谈不上手机、电脑、没有Wifi,更打不了王者荣耀,但是我的童年并不孤独,因为那时候我的童年像一艘五彩斑斓的小船,装满我许多趣事、傻事。
如今我已过耳顺之年,美好的童年已成为遥远的记忆。然而,童年的影像却仍旧在大脑里不时地回放,浮现那剪不断的童趣情怀,想来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,一桩桩,一件件依然记忆犹新。
一、拔秧并非为助长
在我小的时候,母亲经常用勾担挑着两个箢子,前头装着妹妹,后头装着我去赵家南尹村走姥娘家,有时直接把我送到村东的瓜地,让看瓜的老姥爷照看我。
我在瓜棚附近尽情玩耍,热得满头大汗,老姥爷走过来,用手拍开一个拳头大的西瓜,说:“虫子把西瓜秧咬断了,给你个‘死秧子’瓜解解渴”,望着红红的西瓜砂瓤,我馋得直流口水,连忙接过来,三口五口把瓜皮都啃得透亮。
第二天下午我还想吃西瓜,可不见老姥爷再拿瓜来,猜想该死的虫子没去咬断瓜秧吧,只要瓜秧死了,我不就能吃到甜甜的西瓜了。

于是,我趁着老姥爷不注意,两只小手使劲连根拔起一株瓜秧,然后又插在泥土里,再捧上一捧沙土盖在秧根部。不一会儿,老姥爷摘下一个西瓜给我:“瓜还不熟,该死的大牙(蛴螬)这次真的把瓜秧咬断了。”
接连几天死瓜秧,老姥爷很纳闷,说:“好奇怪啊,不多不少每天换着窝咬一棵,这条虫子成精了。”
这天早上,我正撅着屁股拔瓜秧,忽然感觉有人轻轻拍打我的小屁股,回头一看,老姥爷哈哈大笑,说:“我终于逮着咬瓜秧的大虫子了。”
二、“打洋油”误买了酱油
我出生在尚未通电的年代里,小小煤油灯,是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照明灯具,那盏桔黄色、昏暗微弱的煤油灯光照耀着我的心田,令我难以忘怀。
我的爷爷、奶奶过世早,母亲忙着照应我的弟弟、妹妹,把我和哥哥送到伯父家寄养。贫穷落后的乡村,严冬的夜晚是多么的漫长难熬,没有火炉,更没有音像之类的娱乐设施,伯母点燃一盏煤油灯,一边在灯下纺线,一边教我和哥哥唱童谣:
拖拉机,来耕田,
大小干部过个年
大干部吃,小干部尝,
社员尝尝减口粮。
听罢童谣,伯父接着给我们讲述周边的地名故事,说很久以前,西庙的和尚欺男霸女,无恶不作,经常把路过的少女抢去藏在洞里,从此就没了下落,因寺庙主持是皇亲,老百姓义愤填膺,多次上告都被官员层层包庇,后来惹的皇帝也不耐烦了,在奏章上签批“罢了,罢了。”
老百姓一听“罢了,罢了”认为皇上恩准将和尚给“耙了”。
于是就把作恶多端的和尚捉来,埋在地里只露着头,套上牛拉着耙来回耙地,和尚的头颅一个掉下来,血流满地,地越耙越深,就形成了‘和尚汪’。”
地名故事讲完了,伯父只好改讲神话故事,那些吓人的故事情节,我听的耳朵上快要起茧,一个接着一个,还想再听,伯父说“明晚再讲,明晚再讲,早睡早起!”
为了给我们讲故事,伯父借来一本《聊斋志异》,我抢先搂在怀里,他不给我讲故事,我就不还给他书。等到伯父讲完故事,我在煤油灯下胡乱翻书,不识字只看插画,不知不觉把书放在枕边睡着了,突然我感到眼前冒火火,头发也燃着了,慌忙从床上爬起来:“有鬼,有鬼,大爷快来,有鬼!”熟睡的伯父被我吵醒:“哪里有鬼,这不是从窗棂里刮进风,灯火把书引着了,以后你可不能再点着灯,搂着书就睡了。”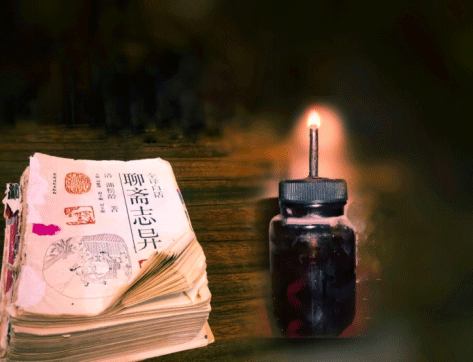
“洋油、洋火、洋钉、白洋布”这些词语让我儿时充满疑惑。到了“打酱油”的年龄,伯父家点灯的煤油用完了,伯母给了我两毛钱,让我去村里小卖部打“洋油”,我误听成打酱油。第一次见到两毛钱的大额纸币,小心翼翼地揣进上衣兜里,走几步就掏出来看看,生怕丢失。来到大队代销店小心翼翼地递出纸币,打了两毛钱的酱油,回到家,伯母哭笑不得:“不知道是我没说清楚,还是你没听明白,咱家需要洋油点灯,洋油瓶装酱油味太大了,不能吃。”
“倒在咸菜缸里吧,腌咸菜总比扔了强,金玉你以后要注意,听话要记清,做事不能马虎。”伯父连忙给我解脱。这一夜没有油点灯,屋里黑灯瞎火,一家人只好早早趴在被窝里,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,伯父“做事不能马虎”的话语回荡在我耳边。
三、同伴偷瓜我策划
我天生胆小,偷瓜摘桃的事不敢近前,但也曾帮助小伙伴密谋过一次成功偷瓜的行动。
那是夏季的一天,天气非常炎热,我们一起割牛草的小伙伴实在口渴了,望着眼前碧绿的瓜地,星星点点的黄色小花下边隐藏着大大小小的甜瓜,可是畏惧看瓜的 “扬大锤”,不敢贸然行动。
“扬大锤”本名王夫新,为人耿直,脾气暴躁,只要他看瓜,别人就别想近前。我们猫在瓜地西边的玉米地里东瞅瞅西望望,刚刚露头就被扬大锤骂了起来:“恁这些小龟孙,想偷瓜?看我不拧掉你们的耳朵。”我们连忙缩回玉米地,不去偷,馋虫上身不忍离去,去偷,又怕被扬大锤捉住。年龄大的德鸿催着我快想办法。
我说:“瓜地里就扬大锤一个看瓜的,咱们可分成两组,一组在瓜地西边的靠近瓜地佯装偷瓜,让看瓜的来撵;另一组沿着河边向东走,从北边爬上瓜地,偷到瓜后迅速下河跳进水里,另一组顺着河水游过去找偷瓜的汇合。”
“真是好主意,就这干。”我的想法立刻得到大家赞同。我身子骨小,力气不大,又不敢进瓜地,所以德鸿特指派我站着放风。
对此“大个子”良存立刻表示不满:“你可……可……怪好,让俺……俺去偷瓜,你看二行?你不去……把把……裤子脱脱脱……脱下来,装……装瓜,要要……要不,你别别别……别想吃瓜!”
我只好把大档裤脱下来递给他,当时农村孩子都没有内裤穿,一丝不挂的我顺着青纱帐奔向瓜地西北角,去站岗放哨。
接着小伙伴们兵分两路,德鸿领着几个小伙伴,从西侧接近瓜地。扬大锤一看,一边追一边骂:“恁这些小杂羔,又来了。看我不抓到你打屁股!”
德鸿指挥着小伙伴不紧不忙地钻回玉米地,故意惹怒“扬大锤”。扬大锤扭头一看,北边的几个娃娃已悄悄溜进瓜地,远远望去“大个子”用瓜秧扎上裤腿,将 “人”字形的瓜袋骑在脖子上,带领着怀揣腰掖甜瓜的小同伙,一溜烟逃向河岸,这位看瓜老人眼看追不上,站在瓜地中央气得直跺脚,破口大骂。
到了河边,“大个子”解开装瓜的裤子腿把瓜倒进水里,小伙伴们扑通扑通跳下水,用清澈的河水洗净甜瓜,大口吃瓜解渴。
初次偷瓜,分不清生熟,连带毛的嫩瓜也摘了下来,苦的不能下咽,实在吃不了的瓜,如果带回到家当然少不了臭骂一顿,弄不好还要挨鞋底打屁股。小伙伴们再次按我的提议,用嘴咬开甜瓜顶,然后插进手掏出瓜瓤灌进湿沙,再埋进浅水沙滩。
我穿好裤子准备回家,谁想粗布裤里沾满了瓜茸毛让我下身直痒,用手一挖,起了一串串过敏疙瘩。
第二天去河边割草,瞧见扬大锤站浅水汪里,一边捞瓜一边骂:“这些小粗鬼,吃不了埋到河里,真会糟蹋人!”
听到咒骂,我为自己出谋划策促成了这次偷瓜行动,羞愧的低下了头。
四、淘气的小学童
我小学一年级的教室是租用季家南尹的泥土房,西边不远就是龙王沟,临近暑假小伙伴趁着课间休息,跳进小河里扎猛子 ,学狗刨。
其实那时家长是不大管我们下水洗澡的,但是学校的老师考虑到安全问题,却禁止我们下河洗澡。我怕受到老师批评,边催促小伙伴赶紧上岸,边爬上陡坡来到教室里。上课铃声响了,迟到的同学一个个顶着湿漉漉的头发,光着脊梁来到教室门口,均被姚老师指派到教室外的墙根罚站,过了一会排着队进教室检讨,听到后边的同学小声嘀咕,我担心露馅,举手发言:“对不起,老师,我也去洗过澡了。”
“啊,你带头去的?为什么别人的头发都湿了,只有你头发是干的?”
“我怕被您批评,只洗身子,没洗头。”
一向严厉的姚老师上下打量着我,脸上绽露出慈祥的笑容,对我说:“无论洗不洗头,下河洗澡都不对,今天饶了你们,以后谁也不准再下河洗澡,否则,我先处理你这个班长。你快喊‘起立’,上课!”
农历十月十五,母亲给我两毛钱去探沂赶会,我迫不及待地到书店花了一毛八分钱买一本《小英雄谢荣策》儿童画册,回到家里把剩下的二分钱又交还给母亲。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画册爱不释手,直到翻的破旧不堪仍不舍得丢弃,后来因搬家遗失,我还大哭一场。

我们升入小学二年级,搬进了村南北大街西侧的三间草房,夏天教室西侧种植的植物麻气味太大,熏得我们上课都不安心。下了课男生们常跳到麻地西边的窑汪里洗澡,女班主任尉(读 yù )老师就让我们班委代她监管,于是我在家做了杆木制红缨枪,课间带着其他四名班委巡逻。星期六上午下了最后一节课,七八个男生就迫不及待地跳进窑汪里,看见巡逻的来了,衣服也顾不得穿,光着屁股钻进一人高的青麻地里,我们把他们的衣服藏在石窟窿里,继续围着青麻地周边巡逻,同学们一露头,我们就大声呼喊,直到太阳快要落山了,我们才把衣服归还给他们。
过去,村里生下男孩有留胎发编成辫的习俗,俗称 “八十辫儿”。王克朋是他母亲生过两个姐姐之后,接连夭折几胎才留住这个宝贝儿子,从小留住八十辫儿,课间还要回家吃奶,我对这个娇生惯养的同学十分反感,借用现代京剧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中反派人物野狼嚎,给他起个外号,编个顺口溜戏弄他:
“王克朋,野狼嚎,八十辫,一撮毛。”
没想到被同学们广泛传唱,王克朋回家哭诉着要他父亲找我算账。王克朋的父亲细高个,漫长脸,声如洪钟,人送外号“真迷惑”, 护犊子是村里出了名的,当天下午上课前他就扒着教室门口,大声训斥:“哼!谁给俺家的小子起的‘野狼嚎’?你给我出来,看我不撕裂你的嘴!”
顿时教室里鸦雀无声,同学们面面相许,一个大气也不敢喘,我脸上火辣辣的。在老师的劝说下,“真迷惑”怏怏离开,下了课,我受到老师的批评,主动给王克朋赔礼道歉,很快我们俩成为了好朋友。
五、露天电影余味长
那时没有家庭作业,农村文娱生活又特别匮乏。放学后一群小伙伴踏遍左邻右舍的房前屋后,撒欢地追赶奔跑、做游戏.....
最大的奢望是看一场露天电影,一听村里来了电影放映队,我放下书包,就空着肚子扛着板凳到大队部广场护位,只见放映员在两根木杆之间,拉起一块大大的四方白布,用绳子牵住幕布的四角,银幕的对面已经坐满了有许多人在等待了。

当发电机“突突突”地响了,台下一双双眼睛开始齐刷刷盯着银幕,先放新闻简报,而后才是正片,中间穿插农村大队长讲话。
村里放电影的次数出奇得少,放映基本是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等现代京剧样板戏,偶尔也放《南北战役》、《地雷战》等战争题材片。感觉不过瘾,我就和小伙伴成群结队到邻村再复习一场。
一天晚上,邻村的大队长陪放映人员喝醉了酒,语无伦次的讲起了话:
“社员同志们请注意,社员同志们请注意,明天早上去耕地的,扛着牛撵着耙,一定让牛把人管得好好的。”
惹得观众笑得前仰后翻,接着这位大队长边哭边诉:“我从三岁没有娘,俺爷把我拉扯大不容易……”
听到大队长失声痛苦,观影现场顿时安静下来,开始放映了。
一场电影结束,并不是真的结束。我们可以对一部电影津津乐道好几天。
六、墙头水饺留余香
在那物质生活极为匮乏的年代,倘若是能吃上一顿馒头,外加一盘炒鸡蛋,就算得上是顶级美食了,更多的时候,吃的是红薯干煎饼,就辣疙瘩咸菜,油水少,腹内饥肠辘辘,那是常有的事。所以要说那时我最想吃的美食,就是邻居从墙头递过来的水饺。

那时俺家一两个月才能吃上一顿水饺。母亲下熟水饺,先从墙头上递给西边邻居一碗,然后再自家享用,同样,邻居陈二婶家里包了水饺,也是通过墙头送过一碗来,让我们分享。我兄妹五个,邻居送来的水饺每人只能分到三四个,但吃起来味道特别美。“墙头水饺”作为左邻右舍和睦相处的象征,浓浓乡情承载着满满童年的记忆。
最拉馋的要数除夕夜的猪肉汤。每年除夕,父亲回家带来一挂猪下水过年,大家一起动手刮净猪头上的毛,洗净放在锅里煮熟了,捞出来把猪头肉切碎,把猪肝切得比纸还薄,然后回锅添上满满的一锅水煮开,每人盛上一大碗猪头汤过年,剩下的再冷成一盆猪头冻,一家人每天只能吃一盘,留着吃到元宵节。
七、我是公社小社员
每天早上我听着村里高音喇叭的革命歌曲起床,伴随着《我是公社小社员来》儿歌走进学校。
我是公社小社员来,
手拿小镰刀呀,
身背小竹篮来,
放学以后去劳动……
到了小学四年级,每个星期五下午便是劳动课,我便当起了真正的小社员。从河沙滩向学校操场沙池里抬沙,用三鲜汤(人粪、尿加水)给蔬菜地浇埋施肥,忙的不亦乐乎。每次劳动课后,老师就要布置我们写一篇作文。记得一次作文课,语文老师先学习《大众日报》记者报道我村王大娘《手捧牛屎不嫌脏,一心向着共产主义》的通讯,接着点评学生写的《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》,我的作文第一次当作范文宣读,真是激动不已。老师讲评道:
同学们学写记叙文不但要体现六要素,还要书写规范,避免出现错别字。
比如有的同学本意想写同学们用三鲜汤浇菜地,干得热火朝天,浇一会,累了就歇一会。结果写成“浇一会,喝一会,人粪尿能喝吗?”
还有一个同学写学雷锋做好事,受助老人说:“谢谢你,小朋友!”我说:“不用谢,不用谢!”结果错写成“射射你,小朋友。”我说:“不用射,不用射!”
老师寓教于乐的讲评妙趣横生,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、眉开眼笑。
我小时既怕遇见蛇,又怕蚂蟥(水蛭),蛇虽可怕但很少见,但潜伏在稻秧田水中的蚂蟥却令人防不胜防。

暑假我坐着小板凳拔稻苗,忽然感觉腿上像有一个东西,低头一看,是条蚂蝗,它用身体前后端的吸盘,紧紧叮住我小腿皮肤吸血,拽也拽不掉,这时母亲过来用力一拍,蚂蝗就掉落在水里。

我吓得蹲在四条腿的小板凳上再也不敢下水,随着板凳缓缓下沉,我一屁股坐在水里,一骨碌爬起来冲到路上,无论母亲怎么劝说,我再也不去拔稻苗了。
生产队长季振方听说后,让我去牵牛耙地,说只要在稻田里不停地走动,蚂蟥就吸不上人身上了。我很高兴接受这项新任务,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牛栏,饲养员王大爷把人们最好使唤的大牯牛的缰绳递给了我。
这是一头我们生产队喂养的南方大水牛,长得又高又大,养得膘肥体健,正值壮年。两只牛眼,铜铃似的;一对犄角都向内弯曲着,像一个没封口的半圆形;四条腿黑而粗,像四根柱子;一身牛皮紧绷绷的,色如大象。
我第一次心惊担颤地牵着牛缰绳,手在不停地发抖,没想到大牯牛十分温顺,按照我发出的“得儿驾,弯、弯,吁、吁” 的指令,用力使劲、拐弯、停止,和我配合的十分默契。
大牯牛不但劲头大,也很舍得卖力气。它前后腿踏进稻田里的烂泥中,瞪着圆鼓鼓的大眼睛,喘着粗气,拉着耙围着稻池子一圈又一圈地转,从不耍滑偷懒。
我给这头心爱的大牯牛起个名字“牯子”,避开母亲从家里抓两把喂猪的豆饼装进兜里,等中午歇歇的时候,撒进大牯子爱吃的青草里,它吃完饲料就趴下去闭上眼睛,有滋有味地咀嚼起来,满嘴直冒白沫儿。

每当我来到牛栏喊一声“牯子”,它就仰起头来,鼻孔里尖声发出“鞥[ēng ]、鞥”应答,我拍一下它的牛头,它就跪下前腿,头伏在地上,我爬上了牛背,然后我用腿夹紧牛肚子,牯子就抬起头,再站起身驮我漫步前行,到了稻田边,它又一次跪下前腿,让我从牛脖子上滑下来。
收工归来,暮色中我仍骑牛背走在乡间小路上,吸引众多小伙伴妒羡。
1972年放了秋假,生产队长分配我和同学王太元到南岭看红薯,地点位于西岭头大渠道的北侧,薯地西侧和、渠道的对过分别排列着一座座土坟,阴森恐怕;新刨出土的红薯个个穿着深红色的睡衣,静静地躺在薯沟里。我俩用薯秧在薯地中间堆砌个U圈,下边铺上麦蘘,上边遮盖上一领苇席,天刚黑就钻进这个低矮潮湿的窝棚里,为了壮胆,再拉过来一捆薯秧挡上窝棚口。第二天早上爬出来,吃着煎饼就着咸菜,再到渠道里喝两捧水,下午带的煎饼吃光了,就想法挖土窑焖红薯。

我们先在土坡下面掏一个窑洞,再从上面开挖一个圆圈,把土掏出来与窑洞贯通,然后捡来土坷垃摆放在上口的周围,一层一层地垒起来,逐渐收口,再用最大的土块封顶。接着捡来豆秸、干树枝放到窑里点着,直到把土坷垃烧得通红。再把下面的碳火全部拨拉出来,掀开盖顶的大土块,小心翼翼地把红薯放进去,然后把烧红的土块捣下去,用撅头砸碎土块,盖上湿土焖上一个多小时,慢慢拨去上面泥土,这时焖熟红薯的甜香扑鼻而来,我俩也顾不得烫,用沾满土灰的手剥皮就吃。
一九七三年一月,我以全学区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探沂公社南徕庄铺联中初一就读。步入少年时代,我的生命之船进入到一段和缓宽阔的新河道,前景徐徐展开,光芒冉冉升起。

追往事,叹今吾,春风不染白髭须。
童心在,不觉老,不知不觉到老年。
童年的时光虽然美好,但我没有留下一张图片,一段影像,只能在记忆里回想了,而我的童年趣事远远不止这些,一个又一个的片段,无不充满着欢声笑语、幽默搞笑,就像一粒粒珍珠,串起了我美好的童年,注定成为我一生难忘的那份精彩。
2024年11月28日于沂蒙小调文博园
注:①文中有些人物不便用真实姓名,假借他名取代。
②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,侵权立删。